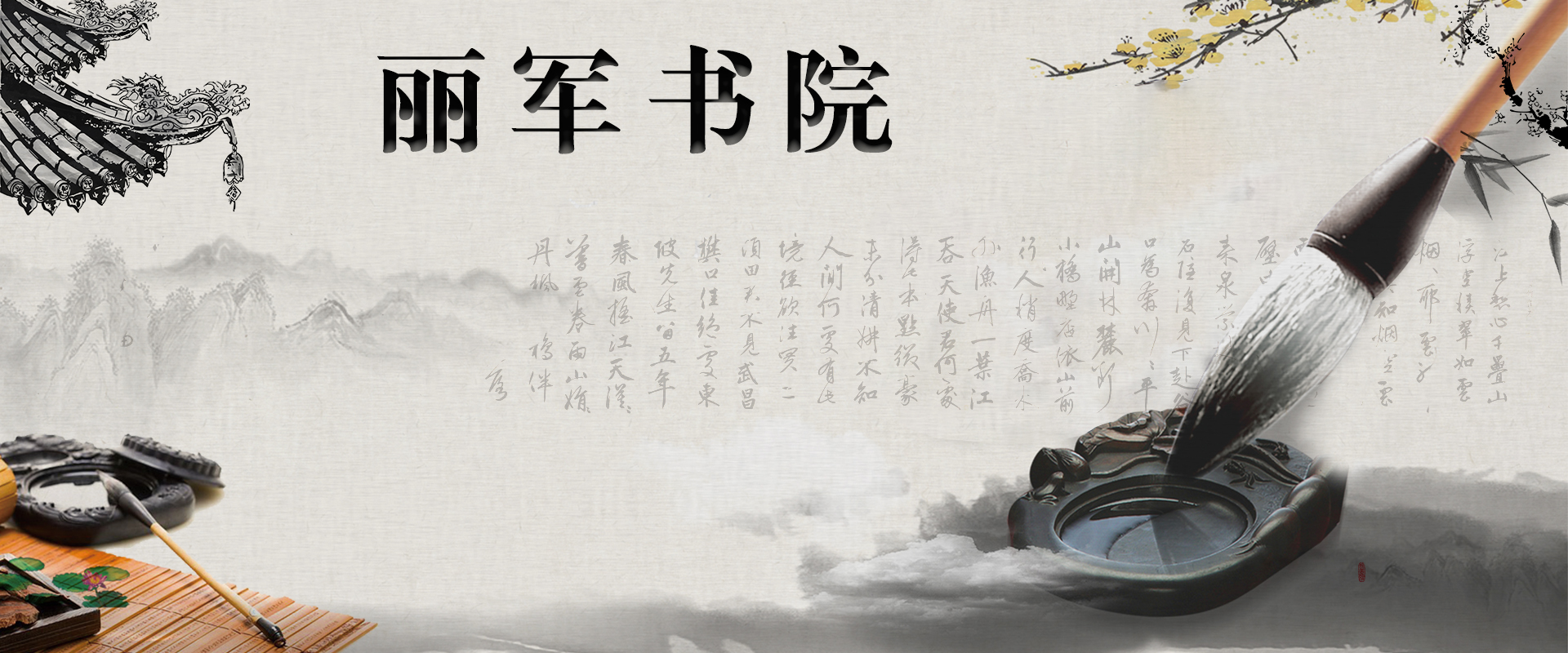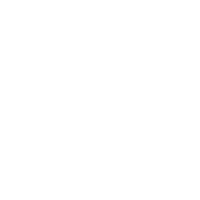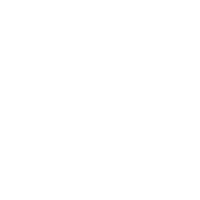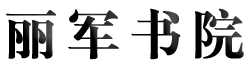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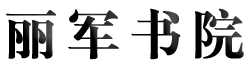
中国文化与中国书法
编辑:2021-08-19 11:09:51
中国书法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迹化形式,并在现代中成为艺术对话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中国古典书法美学精神是重要的。它在现代书法美学所推进回归感性、回归生命、回归人的整体的审美活动中,使现代人禀有了一种强烈的寻根——“寻找家园”意识。它不仅使中国人在书法这一“写意哲学”中体味抒情写意的风神,而且也使西方现代艺术家在目光东移中,找到了精神流离之后的“艺术家园”。然而,中国传统美学范式的局限性,又使得书家和书论家们急于清理根基而使书法禀有“现代”气息。当然,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处身于传统之中又超越于传统之外。
中国文化注重人文精神,肯定人性之善,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中国人文精神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心、人文精神为依,内外兼修。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的升华完成。
文化是“人化”与“化人”。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在于,就本性而言,文化价值不属于物化领域,而是表达一种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追求,反映一个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而文化重建不是固守传统或唯新是求,而是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因为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书法是人的书法,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和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的审美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书法的文化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人的开放性使书法这一国粹成为走向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艺术话语。
中国书法是一种体验生命本体的审美符号。它浸**于中国古老的哲学美学之中,在笔飞墨舞的音乐律动中完成一种时空的审美形式,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为洞悉中国文化精神和华夏哲学美学品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化视界。
古老的中国书法伴随文字的生成和意义的交流而出现,又伴随着抒情达意和文化转型而向今天的人们显示其魅力。它召唤当代书法美学理论家为其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重新审视书法艺术并加以文化定位和价值厘定。
当代书法艺术的价值定位与整个的文化思潮紧密相关。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影响弥深,并生成和发扬为具有本土特色的书法形式(如日本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墨象书、前卫书法),进而导致中国现代书法受日本现代书道影响的“影响的焦虑”。同时,西方也在“发现中国书法”的惊喜中,吸收中国书法精髓去拓展他们的抽象绘画和现代、后现代艺术。于是西方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新画种——“书法画”,甚至有些画家被称为“西方书法家”。
因此,国内有些学者对这种中国书法界与各国艺术家共结笔墨姻缘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也有学者对中国书法的价值定位并不高,认为“书法越来越由中国文化的视觉实在而蜕变为一种民族的历史陈迹或一种古董,换言之,书法的价值不在其艺术性而只在其历史性”。“而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中国书法的赞美和吸收恰恰代表着一种对无意识文化超越的决心;正是因为西方人有这种否定自我固有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勇气,他们的艺术才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革命性。”
无论是对中国书法影响他国艺术感到欣慰还是感到不满,都只是停留在书法价值厘定的表面。在我看来,正因为书法艺术精神是哲学精神的,因而是解放、自由的,是一种心性之美、哲思之美、生命力之美。正惟此,日本学者井岛勉在《书法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中说:“书法是一门以书写文字为中心而形成的艺术,但与其他艺术一样,作为艺术的书法,不仅仅是书写文字而已,它要求由此认识自己本来的生命。就艺术要求的认识生命而言,书法可谓**纯粹、内涵的艺术。流动的书法线条,正是传导生命节奏的标记。”“它的备受欢迎的主要前提是因为恢复了书法艺术自由的创造精神和认识了现代的人类生命。简言之,在现代的环境中,它们再现了书法的本源。”(《日本现代书法》)
同样,英国文艺批评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说:“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不过是中国书法的表现主义的扩展和苦心经营而已。”他在为美籍华人书画家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一书第二版作序时说:“次拜读蒋先生的著作时,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美学与现代‘抽象’艺术的美学之间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西方解构主义哲学诗学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清算和对“书写”的高扬,使得西方学者得以重新发现东方书法的魅力。不了解这一重要的文化哲学氛围,对书法的深层次理论探讨就显得失去了时代文化背景。
法国当代思想家德里达是后现代的风云人物,其解构思想非常复杂。在《文字语言学》(1967)一书中,德里达对张扬言说、贬抑文字书写深为不满,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同样的秩序控制着文字观,而形成“语音中心主义”。这种认为语音(说话)优越于书写的二元论语言观,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语言观”。德里达指出,言语也同样具有意义含糊性、不确定性,在特定场合,说话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语的复述。反过来看,书写也并不绝然成为思想的蹩脚的复述。书写胜过言说之处在于,它的物质铭刻性具有阻断在场的能力。事实上,书写以铭刻的方式,维持了一个符号持久的知觉而禀有一种时空超越性。唯文字能永葆不灭,每一次阅读都将使作者在言说中“出场”。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到了边缘,而书写则上升到新的重要地位。
这样,在中国人准备以拼音取代汉字以向西方人学习时,西方人却以惊喜的眼睛发现了非拼音文字的书法而惊慕不己。艺术家们发现:以团块、光影、透视色彩所构成的西洋画,以对现实尽善尽美的摹仿为能事,竟显得这样板滞和了无趣味,从而打破透视律,以书法线条取代立体光影,以水墨晕彰代替色彩涂抹,以线性笔意的抽象打破团块结构的具象。于是,在新的抽象画中,人们领略了中国书法的风神意态和笔情墨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经历史沧桑的书法就完美无缺了,相反,中国古典书法走向当代,已经和正在发生审美转型,无论是用笔、用墨、结体、章法、乃至墨象笔意,气韵灵性都发生着新的改变。随着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形成,书法也将不断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种转型不是抛弃和重设,而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点上扬弃和再生。因此,文化转型中的书法艺术将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它不是"现代书法"所能囊括尽的。它将一种“现代性”精神质素植入书法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的品格中,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和审美韵味整合在新的艺术形式中,生成新的多元多向的自由艺术范式——“现代性书法”。
“现代性书法”与“现代书法”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现代性”是一个文化美学范畴,指一种精神启蒙质素,一套价值生成模式(哈贝马斯);而“现代”则是一个线性历史范畴,指一段历史时期,或一种历史思潮(杰姆逊)。可以认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将在新的历史契机中,使现代性书法成为现代人的心性灵魂的呈现,成为现代文化价值生成的审美符号,成为现代****的变革过程中不断嬗变流动的艺术精灵。那种认为中国书法因西方没有一门“书法”与之对应而必将成为弃儿而遭致衰亡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也许,正因为,它才会在东方和西方成为新世纪文化复兴的宠儿。
几千年传统书法理论和实践滋养了二十世纪书法美学和书法热潮。在新的世纪,当代学人对中国书法美学的思考和对传统的吐纳所留下的书法艺术精神遗产,必然令后学回味再三。中国书法学有没有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有,这个体系的理论形态是什么?它在今天遭遇到怎样的挑战?其价值重新实现的基点是什么?这些都是书法文化理论必得直面并加以回答的。
我乐意指出,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当今,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东西方“邻居”间互不了解、相互抵牾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文化将寓清新刚健的人生意识和高蹈执着的个性自由于现代性阳刚之美中,从而能够体悟宇宙创造生命的艺术魅力;中国新世纪书法将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融线条和意象于飞动简劲的节奏韵律中,去感悟现代人的超越精神和宇宙大化的生动气韵;中国书法新形式将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风范、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融注在一个自由充沛的自我中,以强化了的主体意识去领略沉思感悟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潇洒美。
中国书法的现代文化品格是充满魅力的,而创造“现代性书法”的历史重担落到每一位中国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面前。
中国书法,以线的飞动、墨的润华,心手相合,抒情写意,划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轨迹。依这一轨迹而行,可窥其文化生命的幽妙之境。中国书法是人生境界和生命活力的迹化,是东方哲学意味的艺术。在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和新世纪将临之时,中国书法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那么,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书法艺术中去,去领略书法构成的艺术魅力,去追溯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去把握书法艺术中所显示出的艺术审美精神吧。
--太原书法培训
联系电话:13693298365(北京)
15035192158(太原)此号微信咨询
一部: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中央团校旁(万寿寺地铁站)
二部: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富力城分校旁
(北中环与东中环交汇处)胜利东街鼎盛国际青创城